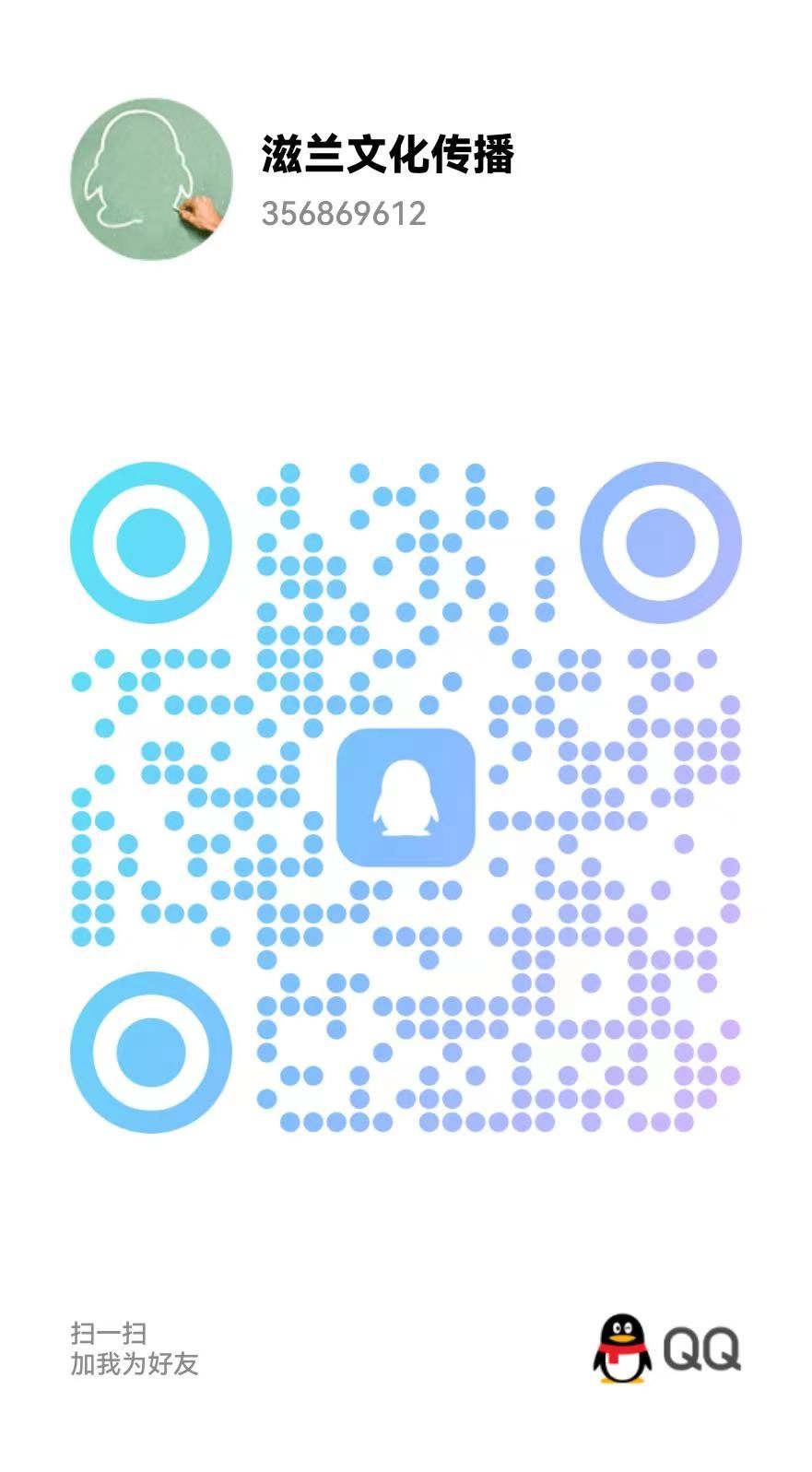古人在表达时间的时候,都很讲究,总显得格外的雅致。如果用“元
丰五年”,那显然是要记载历史了,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,有且只
有一个“元丰五年”;而“壬戌之秋”呢?全部的时间里,有六十分之
一都是“壬戌之秋”,那究竟是哪一个?非考究而不可得知。然而,对
于苏轼一生来讲,这样的“壬戌之秋”大概也只能逢着一两个吧。用“壬
戌之秋”来记时,表明作者即将记录的事件对于人类历史来说,可以微
不足道、忽略不计,但是对于苏轼的一生来说,却意义重大。“乌台诗案”
北京四中语文课 284
大概是要被作为有且只有这一个的历史事件,记录进“元丰二年”的历
史的。苏轼或许是不愿意再提及而有意逃避吧,本该记作“元丰五年”,
他却在自己的《赤壁赋》里提笔写下“壬戌之秋”。年号记时,多少有
点儿唯君、唯上;干支纪时,多少带点儿自我色彩。
还有“既望”。望,每月阴历十五;既望,阴历十六。倘若古人将
每月的“望日”直接说成“十五”,便少却了能引发出关于月和望月人
的许多联想的浪漫,少却了明月底下一尊举首凝望的或孤独或思怨的剪
影。那这个“既望”呢?尽管俗话说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”,但毕竟是“望
完了”“望过了”;也许月正圆呢,但情已阑珊了,兴也阑珊了。
之前读《赤壁赋》,我一直有个疑问:苏轼为什么不在“望日”游
赤壁,而非要在“既望”?是行程的无奈,还是情与景的巧合?我至今
也得不出什么答案,就让这个疑问团成一个无厘头的纠结吧。重要的是,
在我读来,这个秋日的“既望”,实在是合乎一个失意文人的需要。
04苏轼篇2赤壁之游【何止文章-北京四中语文课】OCR识别文字可复制粘贴.pdf